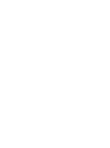余永定: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
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已经使中国经济经历了阶段性供给冲击和外部需求侧冲击两个关卡。在后疫情时代,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风险日益凸现,给中国经济的疫后恢复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也成为政策的关注重点。6月6日,京东数科研究院召开了“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变化和中国经济前景”闭门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出席并做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的主旨演讲。
余永定认为,中国的崛起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必须要打压中国。这是国家利益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能够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好处,导致中美差距进一步缩小,所以美国一定要把中国从产业链中踢出去,特别是涉及高技术的产业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以下为发言全文:
余永定:谢谢大家!刚才听了诸位的发言,收获非常大。其实我们大概讲了四个问题:
一个是产业链问题,我想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在研究全球产业链的时候,我们至少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国内政治因素。这里我指的不是中国,而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导致发达国家的生产者(“蓝领”、“红脖子”)处于弱势地位。本来这些生产者可以和资本家谈判,但现在没办法了,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廉价商品的生产者会与他们竞争,削弱了他们的谈判地位。全球化加速了全球分配不均等,激化了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矛盾。全球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国内传统政治精英、大企业家、金融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传统知识精英也开始首鼠两端。美国政府不愿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和其他政策使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惠及国内广大民众,却把中国当作替罪羊,以转移视线。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反华、反贸易自由化、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化受阻、中国被从全球价值链脱钩都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地缘政治因素。中国的崛起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必须要打压中国。这是国家利益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能够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好处,导致中美差距进一步缩小,所以美国一定要把中国从产业链中踢出去,特别是涉及高技术的产业链。我非常同意黄奇帆市长的说法,这么做代价非常高,美国的资本家会很不情愿,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华尔街的基金公司老板。不过从政治上来讲,他们很难压倒班农和纳瓦罗这样的人。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美国很可能宁可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要保住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或者统治地位。我们不能从“政治家是理性人,不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这种角度来考虑问题。当美国政府看到(或以为)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可能会威胁到自己霸权地位时,他们很可能会宁可自伤一千也要杀敌八百。
第三,产业链自身的技术问题。我觉得刚才方秘书长讲的3D打印机的例子特别好。分工方式同产品自身特性有关。我曾经在重型机械厂工作当过10年工人。重型机械制造的生产工序是要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的。例如,炼钢、浇铸后马上就要铸造;铸造完后马上要锻压,不能等钢锭凉了再加热,那就浪费了。许多重型机械制造品是没有什么全球产业链的。在50年代、60年代以致70年代我们讨论国际分工时的概念是“雁形模式”,是产业间的国际分工。
由于出现了集成电路之类的产品,以及贸易自由化、冷战结束、运输成本下降等因素,全球产业链得以成形。芯片和其它新产品可以而且需要把分工做得越来越细。现在我们研究产业链时一定要考虑效率和风险的平衡。产业链越长分工越细,效率越高,但越长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比如生产一个产品有一百个环节,每个环节出事的概率一样,那么环节越多,出事概率越高,所以最终的解决办法一定是找平衡点。
总之,我们应该从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产品本身这三个角度研究如何优化全球产业链。产业链到底应该多长?不同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产业链?比如大飞机的产业链跟芯片的产业链完全不一样。抽象的原则我们已经谈得不少了。我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对不同的产业链开展不同的研究。我们现在往往大而化之,这是不行的。譬如,是不是能够跟踪集成电路的生产过程,从提炼硅锭、切割成晶圆、晶圆加工芯片、切割成品晶圆、芯片组装、封装到测试这整个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进行细致研究,看看中国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中如何生存和发展?大飞机的全球产业链又有很大不同。它包括液压、燃油、客舱管理与娱乐、防火、信息、线缆、机体结构、金属材料、控制板、起落架结构、环控管路、标准件、非金属材料等十几个系统。每个系统有众多承包商参与制造。在这样一个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必须在哪些系统或环节上具备制造能力,而不至于被人家一剑封喉?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太多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全球产业链时的最大问题是比较抽象,不够具体化。这样,我们就难以提出有实际价值的政策建议。关于产业链的问题,我就先说这么几点。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宏观经济。刚才(祝)宝良提了三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纾困,还是刺激经济?应该采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主要靠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提的都很好,我的基本看法如下:
第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刺激经济增长的阶段,不是纾困阶段。5月之前的工作重心是纾困抗疫,现在已经进入刺激经济增长的阶段,但是这两个阶段不可能划分得非常清楚,所以现在依然有纾困和抗疫的问题要解决,但重点一定是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什么犹豫。我们所处的阶段不同,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一样。在纾困抗疫阶段,政策的重心是保证生产链畅通,保证企业别破产,让人们活下来。这样的话,一旦疫情过去,我们就可以重新恢复生产。如果疫情期间的政策不能做到这点,不能保住现有的生产链,不能让人们健康地活下去,那么疫情过后经济就完了。现在我们国家做的相当不错,基本活过来了。虽然有几十万小企业倒闭,但是总的情况不错。现在一方面要继续纾困,另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上。
第二,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不要说现在,就是在2019年、2018年甚至之前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政策始终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协助财政政策。在经济处于萎缩状态,通货收缩比较严重的时候,货币政策不是很有效,必须用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用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这点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虽然我们央行一直很积极,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但货币政策必须要等财政主角上场后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很多政策可能想的不错,想多做点事,但是,中央银行不是商业银行,不是政策银行,好多事不是它干的事。我不太赞成所谓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提法。货币政策就是宏观政策,央行要决定的是到底大水漫灌、中水漫灌、小水小灌还是关闸不灌。它管不了精准滴灌的问题。
第三,现在宏观政策到底要刺激经济,还是刺激消费?我认为必须刺激投资。过去4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消费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消费主要受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影响。撒点钱可能有所帮助,但是不见得有太大帮助,解决不了很大问题。美国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了钱之后不上班了,另一个是把发的钱存起来或者买股票。日本为什么要发钱?因为日本普通民众的储蓄通常能够维持3个多月的生活,一旦长期不工作就没办法了。4月份东京疫情严重,但大家还是拼命挤地铁。日本政府宣布每人发10万日元后,挤地铁的现象就突然没了。所以日本发钱主要是为了抗疫、纾困。中国已经基本过了抗疫阶段,纾困的问题当然还有。但中国老百姓主要靠社保体系、靠自己的储蓄(特别是那些未被失业保险体系覆盖的人群)度过了难关。在抗疫、纾困阶段(5月之前),我们的失业保险体系发挥的作用差强人意。抗疫、纾困应该主要依靠社保体系。我们现在应该总结经验使这一体系能够更好发挥作用。
发消费券应该是刺激消费(不是救济)措施。我不反对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发消费券,但这解决不了消费不足的问题。消费主要是个内生变量。消费不足同失业有关、同收入预期不好有关。怎么办?就像克强总理说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四个字: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订单有了,居民有了工作,工人增加了收入,消费自然就增加了。靠按人头发钱和摆地摊不是长久之计。脱离经济增长谈就业也是错误的。没有经济增长,怎么促就业?100个人的工作200个人来做?我们要尽快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搞上去,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消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赵敏讲的财政赤字远远不止3.76万亿,还有3万亿是上年节余调整过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财政赤字,所以我们的财政赤字至少是3.76万亿再加上3万亿,也就是6.76万亿了,远远超过我们所说的3.6%。我觉得没有必要躲躲闪闪,大大方方说出来。美国2009年的赤字率是9.8%。关键问题是有没有经济增长。财政部的研究表明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某个界限,财政收入马上下降。为什么要增加财政赤字?第一季度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因为花钱多了,而是因为收到的钱少了,财政收入减少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下去了,因此我始终坚信发展(约等于增长)是硬道理,没有增长一切都谈不上。
刚才杜教授对出口退税的观点非常正确,这是我们在补贴美国。我们已经补贴好几十年了,这种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纠正过来。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