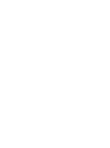彭文生: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有深远含义
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可以说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
近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20年春季会议改成远程会议,这可以说是两大国际金融机构70年来第一次非现场举办重要的年度会议,当然这与全球疫情有关系,也显示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
无接触经济,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不需见面就能完成的经济活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们看到很多此类经济行为,比如电商、生活服务、远程办公/医疗、线上娱乐/教育、在线销售、智能物流等(如图1),这离不开产业信息化、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支持。可以说,无接触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2020年因疫情而发展加速。新模式或技术能多大程度达到商业应用或社区应用,其实和不同路径的成本有关。在线互动的效果可能不及面对面互动,但疫情使得人与人当面互动的成本大幅提高,线下转线上就符合成本收益比了。
疫情过后有些无接触经济的发展可能放缓或不会持续,但这次疫情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数字技术改变商业模式、社会管理方式的时代离我们更近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将带来什么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生产效率、收入分配和公共政策有什么含义?

数字经济增加服务业可贸易性
这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主要发生在服务业。工人不能返工,机器无人操作(除非已实现自动化),相关制造业就难以复工。但通过远程通信、数字技术的应用,一些服务业可实现复工。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制造业是可贸易品,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商品可以跨境流动,但人不能自由跨境流动,服务业往往要求人与人之间互动。这次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人员流动,效果类似国家间的移民控制。无接触经济有助于克服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障碍,显示服务业可贸易的潜力。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的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降低延时等,都增强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研究文献有个流行词Telemigration,可翻译成“远程移民”或“虚拟移民”。一个人没有移民,但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应用被另一个国家的机构雇用,所以叫Telemigration。贸易一般指国与国之间,但大型经济体内部也存在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之分。中国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商品是可贸易的,很多服务业过去是不可贸易的。无接触经济同样彰显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我们要重新思考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传统上经济学对服务业不太瞧得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质疑甚至讽刺乐师、牧师、律师对社会的价值。马克思的《资本论》说,生产活动需要服务业的支持,但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现在人们对服务业价值的认知已发生变化,但有个观点现在仍得到很多人认同,即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慢。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举的一个例子被广为引用,他说虽然有几百年的技术进步,音乐会四重奏还是需要四个人。
服务业可贸易对生产效率的含义

我们怎样理解过去二三十年,尤其是过去10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不仅是美国(图2),还有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学文献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统计误差。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一些经济活动边际成本接近零。比如过去听一首歌需要买唱片,现在通过数字技术无数人可以享受同一首歌,它的边际成本是零。边际成本是零的经济活动不一定体现为货币价值,没有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GDP)里,进而没有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二是通用技术渗透需要时间,就像电发明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的渗透持续几十年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个渐进的过程。三是某个或某些领域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一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粮食生产或冰箱制造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现实生活中人们需求有限,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剩余劳动力,而剩余劳动力一般会转移到生产效率不够高、供给不够多的行业和产品上。由此导致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效率比较低的部门,使得这类部门在整个经济里所占比重增加。按照权重来算,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速就没有先进部门那么快,甚至是放慢的。这在经济学文献里被称为“鲍莫尔病”(Baumol Disease)。即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停滞部门或效率低的部门。也就是说,总体劳动生产率放慢,不一定是没有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生产效率低的行业。一般来讲,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较慢,随着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服务业占用资源增多。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在过去几十年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美国更是如此(图3、图4)。

数字经济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原因包括:一是贸易带来竞争,竞争会提高效率。二是贸易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因为市场规模增加了,边际成本下降。最后,贸易可能带来技术外溢,提高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部分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都假设单一部门经济平衡增长,但现实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并不是平衡增长,发展经济学虽然包含结构转型,但一般只应用于低收入国家。现在数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重新重视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不仅适用于低收入国家,也可能适用于中高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后,提升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和公共政策都有重要含义。
那公共政策怎样提高服务业可贸易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呢?一方面是引导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应如何监管数字经济,避免或降低垄断、促进竞争等。数字经济的零边际成本特征,导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出现了几家科技巨头、平台经济,美国的亚马逊、脸书、谷歌等,中国的腾讯和阿里等,现在也有较大的争议。巨头在成长过程中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会不会成为新的垄断反而阻碍新的创新呢?这是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对发展模式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制造业与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是成功的范例。现在数字经济可能改变背后的逻辑。数字经济不仅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还可能降低了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商品包含两类成本,一是制造成本,包括劳动力等;二是贸易成本,包括运输等。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背后的推动力是制造成本的差异,主要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如果机器替代人会导致什么结果?劳动力成本差异可能就不是问题了,机器替代人会导致制造业回流到高收入经济体,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但同时,数字技术降低了人和人远程互动的成本,使得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增加了,这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深远含义。
现在国际上经济学文献有种观点,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中东、南亚等,想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行不通,未来是机器替代人,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这是比较悲观的看法。但也有相对乐观的,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就服务业而言,发展中经济体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仍存在,这种发展模式就是印度模式。印度以服务业出口而受到关注。中国的出口是制造业,商品贸易顺差、服务业贸易逆差,印度反过来,印度是商品贸易逆差、服务业贸易顺差。这两种模式之争,到底未来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我相对偏乐观,机器替代人不能够阻碍落后国家的进步。但是发展模式需要变革,我们要更多关注服务业。其实不仅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一样,中国东部和西部,上海和贵州,西部如何追赶东部?过去靠制造业转移,东部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机器人的成本下降,靠制造业转移降低地区间的差异,这个模式是否还像过去那么有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更需关注分配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可能影响相对价格。有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简称BSH)讲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增长时,实际汇率升值。这是因为贸易品生产率提升,工资上升,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非贸易品行业工资跟随贸易部门的工资上升,但其生产效率没有提升,导致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上升,即实际汇率升值。同样逻辑也适用于国家内部,大城市价格相对于小城市、农村的价格高,主要也体现在服务业价格高。随着部分服务业变成可贸易品,非贸易品范围缩小,意味着其价格上升压力可能更大。这对收入分配可能有重要含义。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在一些方面降低了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是赋能劳动者,但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的工资并没有跟随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下半叶开始改善,背后有公共政策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作用。按照经济学理论,劳动者的报酬跟随其边际生产率提升,前提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但现实中有垄断问题,有些经济活动有负外部性。
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呢?一是供给有限的行业,由于技术进步不能引入该行业,或者虽有技术进步但某种原因形成垄断,供给因垄断受到限制。这些情况下,其相对价格上升,从业人员收入和资本收益上升。比如专利权在有效期内享有专利租金,人难以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还有房地产,地产是生产效率提升几乎不可能的产业,因为土地不可再生,空间有很强的排他性。二是产品与服务是需求近似无限的行业,人们的攀比消费,比如对时尚与品牌的追求很难用理性行为解释。三是具有零和属性的经济活动,一人所得即另一人所失,这对整个社会来讲不创造新增加值,主要是起到分配作用。即使数字技术提高其个体生产效率,但它是零和的,效率越提高,对方受的损失可能越大。比如,网络诈骗与网络警察、比特币交易、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游说、离婚律师等。数字经济带来部分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按照“鲍莫尔病”,结果可能是社会资源更多配置给供给有限、需求无限(攀比)及零和经济活动。我不是要否认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而是收入分配可能越来越走向极端,需要公共政策的关注。
疫情下的思考
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而且它引导资源配置,会改变成本和收益比较,改变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行为。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引导公共部门投资,比如5G新基建。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次社区防疫显示大数据有助社区精细化管理,但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边界在哪儿?这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最后,贫富差距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新的特征,公共政策该如何应对?技术进步提升效率后资源将如何分配,是否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技术进步慢、垄断、畸形消费需求、零和经济活动上?这些都涉及社会伦理,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绕开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学应该向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所回归,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工业革命时期开启了政治经济学,今天在数字经济时代,在边际效用理论之外社会伦理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应不应该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或类似保障?应不应该增加财产税?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倾向于不可再生的资产,比如上一辈遗留的资产、房地产,这种状态能否持续,怎么来纠正?这些可能都是需要公共政策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