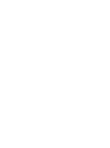赵建:悲情叙事权、地摊经济与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
正能量的权威话语体系下,悲情叙事的权利被谁剥夺了?
-
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
后疫情时期发展地摊经济是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再次救赎。
真正的改变,都是遇到较大的变故之后。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尸位素餐、昏庸无能、喝茶看报的官员被撕掉了“遮羞布”,可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上位。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影响。
“多难兴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要很强的场景条件。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因为只有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才会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最鲜明、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与明显的突变相比,我们更想思考和看见那些悄然无声的变化——城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灾难之后,心灵的创伤更容易让人彼此温柔以待。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更加暴戾,更加相互猜忌和相互伤害。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一场疫情,可以让城市贴上某种伤痕的标签。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然而,这样的记录被一再曲解。文学的深刻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悲剧式反思。当作家失去了为这个城市记录悲伤的权利,只剩下空洞词汇填满的时候,那这一城悲伤的故事,又如何向后世言说?一个染上疫病的城市,原本不幸,为何又失去了哭泣和倾诉的权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恐怕是叙事者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爱惜心才会疼,才会有无尽的忧伤。瘟疫对一个城市的伤害,最深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灾后的城市心灵重建可能同样重要——该如何医治,才能回到从前的人间烟火。
城市应该更宽容,更有温度,更有叙事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城市可以治愈伤痛,那首先是要看到、听到伤痛。
真正有力量的正能量,不是强颜欢笑、漠视病痛,而是直面悲剧、含泪向前。这次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感动来自最平凡的坚守和付出。一刹那偶然的善念,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英雄的城市,也将如同她灿烂如血的樱花。落花无声,一个城市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似乎从来就没有来临。如同生命的逝去,总是落花无声。

然而城市也充满韧性和希望。如同澳大利亚残酷无情的山火,过后不就就有新的绿色倔强的破土而出。在疫情“洗劫”过后的城市,也在慢慢的生长出不一样的颜色。原来被禁止的地摊经济,就像野火后的小草,开始在各个城市,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该如何站在后疫情时期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城市化,以及“地摊经济”这种原始的乡土商业模式在城市的复苏。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的说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最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有人情味、烟火味道的才叫城市,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空洞空间。对一个城市的爱和眷恋,往往只是因为一张无意的笑脸、一次热情的寒暄和一场温暖的遇见。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瘟疫让伟大的思想者从城市还乡,并在乡村成就不朽和伟大。瘟疫从文学和哲学角度重构了城乡关系,让一直在城市浮躁的心灵和思想,回到乡村沉下心来在孤独宁静中重寻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的重建过程,本质上就是从离乡到返乡的一段艰难路程。
所以海德格尔要从城市躲回乡村研习存在。奈保尔回到故乡才找到文学的真义。在疫情和危机时期,城市才希望重新找回乡土。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生病的时候最思念家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反城市、去城市化的:城市在积聚,疫情在解聚;城市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口密度,疫情防控需要降低和稀释人口密度;城市在拉进距离,疫情防控需要拉开距离;城市在深化社交关系,疫情防控在逃避社交关系。城市对距离和空间的定义,不只是地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但一旦大疫情发生,这些意义终将消解。
城市是先进文明的典型空间表征。而先进的文明往往又有脆弱性一面。当危机发生后,乡村往往成为城市缓释危机的重要地带。人在失败的时候总想着回到故乡,城市也一样。
且不论其它国家,中国建国后七十年,每次发生重大危机,都是乡村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三年自然灾害的2000万人口下乡,十年非正常时间的2000万知识青年下乡。以及次贷危机后也是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乡村就像无私无声的母亲,一次次承受受伤的孩子归来。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所以再一次,在疫情造成的大危机中,乡土中国仍然承担起缓释风险的责任,就像历次乡土母亲做的那样。
既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既然曾经的故乡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容纳受伤的“游子”,因此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回到文章的开头,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很多,让城市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广整洁但底层生活购物很不方便的现代景观、表面工程。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可以说,地摊经济是“后疫情+后城市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化不宜太激进,城市化需要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否则政府人为建构的庞大城市,只会更加脆弱——既没有能力防范疫情等重大危机,又没有能力缓释和解决危机。城市也是街头暴力的温床,这在当前的美国等国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