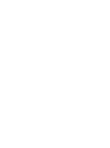读懂傅高义,你才能读懂中国
“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
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对身边一位年轻的研究助理如是说,理由是他从来没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这样的话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她对他的建议是在谋求教职之前,应该去海外,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一番。
 ink="">
ink="">
这是五十年代的美国,这名助理叫“埃兹拉”(Ezra Vogel),刚刚获得哈佛社会学博士。正是弗洛伦斯这些话,启发他的日本之行,一呆就是两年。
随后他还去了中国,在美国和东亚之间穿梭,写了不少关于这个地区的著作。对了,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傅高义”,在其爆得大名的《日本第一》之前,他还写过不少著作,其中一本从人类学视角聚焦日本中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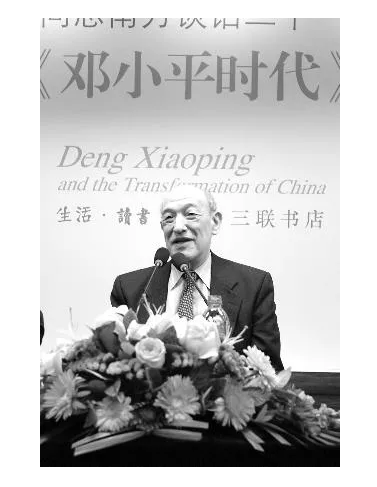
— 1—
这就是傅高义如何来到日本的故事,也是《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诞生过程。由于弗洛伦斯的建议,傅高义决定去了解其他文化。在奖学金的帮助下,他和妻子苏珊娜选择了日本。
虽然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研究并无背景,但逻辑出发点很简单,日本和美国虽然都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文化却完全不同,过去如此,今天似乎也如此。
1958年到达日本,是傅高义和当时的妻子苏珊娜第一次出国。他们第一年时间主要在学习日语,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博士和其太太八千代提供了不少帮助,不仅安排傅高义夫妇住在隔壁,而且充当了导师角色,乐于给傅高义夫妇解释关于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
学了一年日语之后,傅高义夫妇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他们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社区,开始自己的工作,选择了六个家庭,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
这个社区最开始在书中为了隐私舍弃真实名字,以M町代替之,很多日本人看到书都询问是不是写他们,后来才透露是位于千叶县——这些细节既表示傅高义作品本身的生动,也无意间揭示了日本社会的同质性。
千叶靠近东京,依靠便捷的地铁,迄今仍旧聚集了很多在东京上班的工薪族。
— 2—
日本中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商人,另一类是大公司的雇员,所谓新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后者。
工薪族尤其是大公司的工薪族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或者说中产阶级中坚力量,日语中 sarariiman来自生造的英文单词“ salary man”(工薪族)。
虽然这一词汇或者这类人在战前已经出现,却是在战后真正得到重视,他们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地位都得到社会最多认可,直到今天,年轻人渴望加入大公司不仅是寻求经济上的可靠,更是寻求一种社会认同的生活方式。
五十年代时,随着日本公司的壮大,上班族也在扩大,他们的妻子也可以在家作全职主妇。这一典型日本家庭制度模式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在傅高义夫妇观察的年代,这种模式还算是新秩序。傅高义夫妇敏锐地注意到这点,也目睹这一模式从M町扩散到全国。
《新中产阶级》主题所描述的是五十年代末的日本中产阶级生活,从家庭内部以及家庭外部等因素揭示了日本中产阶级生活的横断面。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记录和今天日本中产阶级可能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无论观念还是生活方式。有意思的是,傅高义夫妇和这几个日本家庭保持了友谊。
此后三十年内,虽然傅高义夫妇已经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始终不断重返日本或者在美国与这些日本家庭聚会,这些持续接触更新了他们的研究。
五十年代日本中产阶级处于转变的十字路口,其生活水准正在追赶西方。按照傅高义当时观察,M町这些家庭或许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却还买不起一辆汽车。此刻,他们对于美国生活方式仍旧是仰视和学习态度。
再晚一些,六十年代之后,M町可以负担自己的汽车以及出国旅行,或许仍旧赞许美国模式,但是已经决定选择日本生活方式,其民族自豪感提升很快。
等到八十年代,日美力量的对比改善更为明显,M町居民相当富足,生活水准已经追赶欧美水平;以此同时,对工作压力的抱怨开始出现,个人主义广泛兴起。
一个典型案例是食品,苏珊娜记得五十年代M町的冰淇淋冰多奶少,但日后M町冰淇淋种类和质量提升到媲美世界,有成员抱怨哈佛附近冰淇淋店没有一家赶得上M町水准。
日本中产阶级从五十年到到八十年代的变迁,其背后最大驱动力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在这些记录中不仅可以看到日本中产阶级兴衰,也为中国中产阶级的路线提供参考。
随后的故事发展,大概大家也清楚,从“日本第一”的年代再到泡沫的幻灭,日本迎来“失去的二十年”。
— 3—
至于傅高义本人,则从此与亚洲结下缘分。
他六十年代完成这一课题回到哈佛,在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备受关注之下,他的研究一直没有离开亚洲。日本之外,傅高义也关注中国,并在1973年访问中国。70年代末,他重返日本,写出了《日本第一》。
有的书名气太大,属于大家都知道但是都不太会去读之列,《日本第一》大概也在此列,《日本第一》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也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本书成名多少在于其主题,甚至名字: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本成为世界关注要点,这本书在世界尤其日本风靡一时。但是随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世界对于日本兴趣兴趣降低,对这本书的关注降低,甚至出现了不少批评。
对于外界批判,傅高义表现比较坦然,甚至2000年再度出版一本新书《日本还是第一吗?》(Is Japan StiII Number one?),在重新审视日本模式之余,他重申自己当年是为了美国民众而写《日本第一》。
《日本新中产阶级》某种程度有点类似《日本第一》的前传或者序曲,呈现方式则更为学术更为微观。
如果没有五十年代的田野调查,傅高义对于日本的理解不会那么深入。这些接触不仅让傅高义夫妇理解日本中产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关键是让他们走进普通日本人的世界。这使得即使傅高义日后写作主题扩大到企业、国家与外交等宏大主题,主角变为政治伟人,但是他的关注角度始终包含普通人的想法。
我对于日本经济深感兴趣,在2017年东京访学主题就是中日经济对比。在日本,《日本第一》仍旧是人人皆知的著作,但和当地朋友聊起,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面露尴尬辞色,或许是当下的悲观让他们对于当年的辉煌有些不堪回首。
当我重新读完再版的《日本第一》之后,感觉虽然成书几十年了,结论不谈,其背后的方法论还是颇有可观之处。整体上,感觉傅高义是典型哈佛学者,研究重大受关注课题,人也很有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傅高义对于日本当时优势背后隐藏的劣势也看的清楚,尤其制度变革与社会结构方面,一窥到日本体制诸多弊端。
傅高义始终强调,这本书重点在于,日本经验对美国的意义,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虽然这曾被外界认为是对于预言落空的托词。
不过,站在四十年前情况来看,可以更容易理解傅高义的用心。
对比日本对美国全盘跟踪与保持学习的态度,美国对日本态度往往是俯瞰与输入,二者之间的不对称性导致了美国对于日本成就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充满恐惧。傅高义此刻的写作,大概有着唤醒美国人的作用。
多年后看,虽然部分判断有误,尤其经济方面对我启发不大,但有不少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脱离了文化比较似是而非的窠臼。
— 4—
追溯日本离不开历史视角。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其现代化之旅,其炫目成功之下,仍旧无法掩饰一个特点,其从传统社会和到现代社会时间极其短暂短,类似改革三十年中的的中国。
虽然日本人学习海外素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但期间各种剧烈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在时空转型中压缩在短短时间之内,遗留了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在日后不断发酵,无论是大正时期的暗杀成风,还是昭和上半截的军国主义,抑或日后经济中的集体主义。
回看日本现代转型历史,转型前和转型后不应该割裂,但是过多强调文化尤其传统文化可能并不那么正确,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这体现了思维上的僵化。
如果认为一个国家始终由其文化决定其走向,罔顾其在现代化过程中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诸多努力与巨大变化,这显然有问题。
譬如《菊与刀》是人类学分析典范,也是日本研究的必读之作,直到今天读来仍旧很多启发,但是这本书是战争时期产物,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低估了特殊性背后的一般性。
如果到现在对日本或者日本人的想象仍旧停留在诸多“既……又”之类,只能说是我们观察力不足的失败。
中国人说起日本,知识精英总是惭愧地表示我们对日本了解远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这话说得漂亮似乎成为知日或者知中的惯常认识起点甚至政治正确。不过反过来说,这话只说对了一小半,尚未触及更大的真实。
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有历史与学术传统,日本国内的中国研究在专注度与数量上,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是压倒性的;当然其水准也参差不齐,日本传统上对于中国误判也不止一次。
更值得思考的是,国人不了解的国家恐怕不只限于日本,其原因看似中国国民性,其实和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关,这话远了,这里不谈。
外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类是立足本国(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看日本,这往往是国内日本传播者的最大弊端,其结果往往是粗糙的比较与草率的结论;再高一点是努力做到立足日本看日本;而更高层次,其实应该做到跳出本国和日本看日本,以新鲜的第三方眼光看日本。
傅高义的两本写日本的书,《日本第一》虽然是立足美国看日本,导致其观察与结论存在偏差,但是因为有跳出美国和日本看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作为底本,傅高义的思考和写作始终高于同侪,在直接对比和超越对比之中做到了平衡。
— 5—
近年来,我和不少美国、中国朋友交流中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不少人似乎觉得世界中心除了美国就是中国,伦敦已经不是中心,日本更是往事。
我们过去有不少批判美国普通人对于世界不关心,以美国为中心的思维狭隘,但是时代一换,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些朋友也难免陷入同样的思维惯性,“中国中心”和“美国中心”比起来似乎是五十步一百步,似乎接受了美式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美式的狭隘。
毕竟,仅仅了解一两个国家其实很难真正了解世界,文明的可贵就是多元与复杂。
傅高义之所以去日本,既有弗洛伦斯的一语点破,也和他一贯的训练有关。他深信人类学的价值,“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
这个意义上,《新中产阶级》作为一本优秀民族志,无论时代更迭,热点起落,在日本研究中始终不可忽视。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弗罗伦斯的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弗罗伦斯的话让我想到诺贝尔奖得主V.S.奈保尔的思考,“这个作家的看法是以什么为基础?他了解哪些别的世界,他把哪些其他经历带进他的观察方式之中?一个作家要是只了解这个世界,他怎么去写这个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具备日本、中国甚至东亚与美国比较视野的傅高义作品,本身比起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书籍具备历史的穿透力。这,或许也正是我们今天还在阅读他的原因。
本文原发于微信公众号“徐瑾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