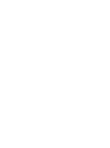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谁在害怕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
 ink="">
ink="">
疫情大流行下,世界上许多央行正式审查其货币政策战略。不幸的是,他们似乎发现需要从所面临的挑战中吸取错误的教训。
最先完成这一进程的是美联储,它决定转向一种新“灵活形式的平均通胀目标制”策略,这是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8月份杰克逊霍尔货币政策会议(Jackson Hole monetary policy conference)年会演讲中所提出的。同样,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最近在第21届欧洲央行观察家会议(ECB Watchers)上表示,欧洲央行正在进行其 “货币政策战略审评估”。而据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透露,目前正与首相菅义伟的新政府讨论如何应对疫情,以及新货币政策战略是否妥当。
从这些讨论来看,此前似乎有一项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行动在进行,每个国家或地区都采取与美联储相似的战略,再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但现在看来已经不是这样了。前首席经济学家、欧洲央行董事会成员奥特马尔·伊辛(Otmar Issing)认为,“至少,其他央行不应盲从美联储的新战略。”
伊辛并不是唯一发现美联储的最新做法存在问题的人。9月初,前美联储理事罗伯特·海勒(Robert Heller)在给媒体的评论中指出,美联储“不应将平均通胀率定为2%”。随后,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本月召开的线上会议中,前费城联储主席查尔斯·普洛瑟(Charles I. Plosser)和贝伦贝格资本市场公司(Berenberg Capital Markets LLC)的米奇·拉维(Mickey D. Levy),均批评美联储没有具体说明衡量平均通胀率的时间跨度到底是一年还是几年。
鲍威尔本人也在8月份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上承认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定义平均数的特定数学公式上,”他补充说,“我们关于适当货币政策的决定不会受任何公式支配。”随后,美联储理事会在同一天的新闻稿中解释说,政策决定将基于“从最高水平对就业缺口的评估”,而不是像之前所说的“偏离最高水平”。
但是,无论重点是“偏差”还是“短缺”,这种新方法都会增加不必要的不确定性,因为它没有定义什么是短缺。 此外,它也没有提及如何使用货币政策来产生更高的通货膨胀,以弥补通货膨胀率低于2%时期的损失。美联储是否正在考虑在当前接近零利率和大规模资产购买的组合之外,对其程序进行进一步改革?
在采取这种“灵活”的做法时,美联储似乎已从至少2017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更具战略性、基于规则的政策上做出了转变。截至今年夏天,其《货币政策报告》不再包括有关货币政策规则的内容。而之前的六份报告则有一个完整的章节,其中介绍了不同的规则,并与实际情况进行了比较。其规则包括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透明设置,包括所谓的泰勒规则(Taylor rule)、价格水平规则,以及应对零界限的经修正的泰勒规则。
可以理解的是,伊辛和其他人将不愿意接受美联储这种做法,尤其是在其他央行可以寻求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走上疫情大流行之前与美联储本身所遵循的基于规则的政策道路,而不是寻求新的或完全不同的东西。
实际上,这比说起来要容易。 当我第一次提出泰勒规则时,该规则已经被广泛讨论了30年,当时我是基于平均通货膨胀率提出的。 但是,与美联储现在采用的模糊定义不同,我明确地将“平均”定义为“前四个季度的通货膨胀率”。换句话说,美联储仍然可以改用平均通胀率的方法,但具体程度远远超出其决定的范围。
此外,先前在《货币政策报告》中列出的正式政策规则都有变量来解释通胀率以外的因素,例如失业率或实际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差距。在不忽略通胀目标的情况下,可以将这些变量纳入当前的战略中,同时也可以纳入处理资产购买及其最终平仓的政策规则。对于美联储而言,制定这种方法并不困难,特别是如果其他中央银行也选择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话。
十年前,我与现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C. Williams)撰写了一篇题为“简单而稳健的货币政策规则”的文章,其中我们强调了基于规则而决策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研究表明了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杰出的货币学者都认可这种方法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央行和其他央行在陈述其货币政策评估时通常会使用“战略”一词。战略方法必定是基于规则的方法,而这正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方式。